契丹的部族管理,南大王院的职能和地位研究,官职体系的职能变化
契丹北、南大王院的职能与地位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。最早对此进行研究的日本学者有岛田正郎和爱宕松男,随后,陈述、蔡美彪、何天明、刘国生、武宏丽等中国学者也对这一话题做出了深入探讨。在这些研究中,何天明和武宏丽的成果尤为突出。何天明在其《试探辽代北、南大王院的职掌》一文中,专门考察了北、南大王院的职能。他认为,虽然这两个机构的职能主要集中在处理本部事务,但它们在北面朝官系统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然而,何天明在描述这些职能时较为简略,并未对北、南大王院的具体地位作深入研究。而李桂芝则从皇位继承的角度分析了大王院大王的作用,武宏丽则全面探讨了辽代北大王院的职能与地位,指出北院大王不仅处理部族事务,还参与国家的军政事务,并且随着历史的推移,其地位有所变化。可惜的是,武宏丽的研究侧重于北大王院,并未涉及南大王院,且未从辽朝职官体系的角度分析北、南大王院职能和地位的变化。总体来看,学界对北、南大王院的研究多集中在某一历史时期的职能与作用上,缺乏对其职能和地位变化的系统性整体研究。

北、南大王院作为契丹重要的部族机构,其起源可以追溯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从迭剌部析分时。迭剌部曾是契丹最强大的部族之一,也是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主力。迭剌部的支持是耶律阿保机能够从夷离堇部崛起,成为统治契丹各部的可汗,并最终登基称帝的重要原因。然而,在他称帝后的第五年(911年),耶律阿保机的几个弟弟在迭剌部的支持下发动了“诸弟之乱”,直至平定叛乱,耶律阿保机才决定宽恕他们,这也反映了他对迭剌部的忌惮与依赖。之后,在天赞元年(922年),耶律阿保机正式登基建立辽国,并在不久后将迭剌部分为“五院”和“六院”,形成了北、南大王院。同时,这两个大王院被纳入两府宰相的管辖之下,意味着其部族管理的核心地位被两府宰相取代。

展开全文
辽太宗即位后的会同元年(938年),为加强中央政权的管理,进行了一次官制改革,建立了南北官制。改革后,北、南二院大王被正式“升为王”,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。契丹政权的建立和发展,离不开部族的力量,因此辽朝皇帝在治理国家时必须依赖北、南大王院的协助。会同元年,辽朝通过收复燕云十六州,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控制力,并设立了新的行政机构。此时,北、南大王院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结构中,成为辽朝政权的一部分,北、南大王院的大王也开始扮演“在朝官”的角色,积极参与国家事务。

辽朝皇帝政权稳固后,北、南大王院的职能在政务处理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,尤其是在宫廷事务与礼仪活动中的参与。如在辽朝的“腊仪”中,北、南大王院的大王需参与贡品的进献,这是部族首领忠诚于皇帝的象征之一。此外,在辽朝的大型建筑工程中,北、南大王院的大王也需承担部分费用。比如,在正月的统和元年(983年),北大王院大王普奴宁就向皇帝“进助山陵费”,表明了他们在这些重要事务中的参与和贡献。

作为辽初“四大部族”之一,北、南大王院大王手握重兵,负责镇戍边疆,这是其重要的职能之一。在辽太祖时期,迭剌部便承担着边疆防卫的责任,尤其是在北、南大王院分设后,夷离堇被指定为其领导,负责防卫并参与军事行动。例如,南院的夷离堇就曾参与镇守西南地区,在边境上对抗敌人。辽朝初期,北、南大王院的职责不仅仅是管理部族事务,它们还担负起了镇守边疆的重任。辽太宗通过设立南北官制和统一治理系统,进一步提升了北、南大王院大王的地位,并将山前后之地作为重要的防守区域交给北、南大王院。

随着辽朝的边防体系逐步完善,北、南大王院的职能开始融入到整个辽朝的军事防卫结构中。特别是在中京地区,辽朝确立了五京体制,北、南大王院开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,成为“北面边防官”体系的一部分。随着契丹的边防体系逐步完善,辽圣宗时期,北、南大王院大王开始在边防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,负责辽朝边疆的防守。这种防卫职能不仅仅是军事行动的指挥,还包括对周边部族的控制和对辽境的维护。

总体来说,北、南大王院随着辽朝制度的不断完善,逐渐从早期的部族管理机构,发展成辽朝边防体系中的重要一员。尽管其职能和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变化,但其在辽朝政权中的作用始终不可忽视。它们不仅是军事防卫的主力,也在国家政权的维护、部族事务的处理及边疆地区的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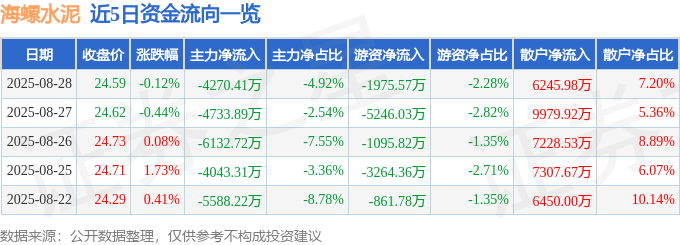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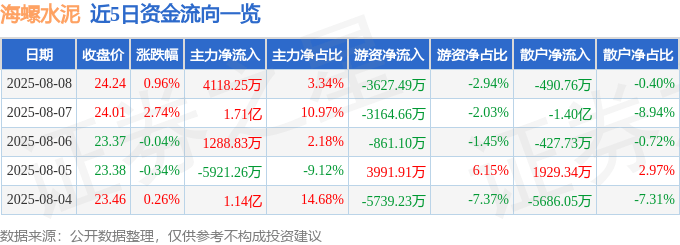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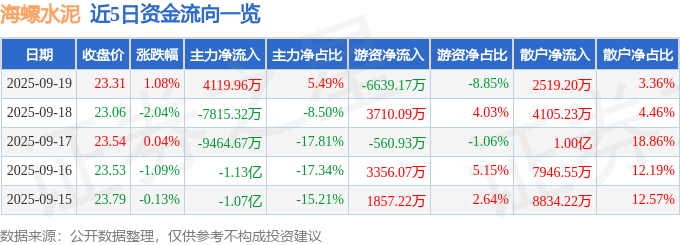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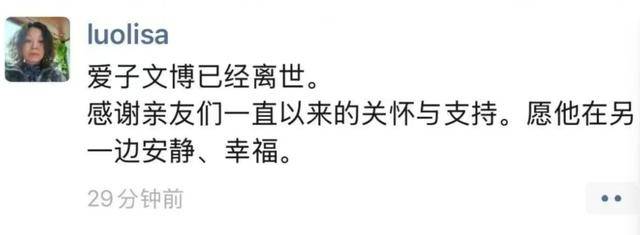


评论